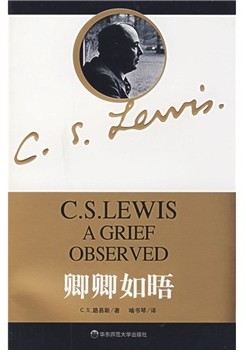
最初,她只是他千万个读者中的一个。他在英国,而她在美国。
擅长写爱情故事的他一直没有结婚,而她,有着自己不完满的家庭。她的丈夫外遇不断,后来,他居然爱上了她的表妹,不得已,他们离了婚。她带着两个孩子,从美国来到英国。就这样,他成了她可以倚靠的朋友。
这一年,他55岁,她38岁。
他们之间有许多密切的往来,但却不关涉爱情。
后来,她在英国的签证到期了,摆在她面前的将是离境,而留下的唯一办法就是与一位英国公民结婚。他决定帮助她,给她一份名分上的婚姻。就这样,两个彼此存有一定好感的人被命运安排成了名义上的夫妻。他们谁都没有料到,他们的关系还能往前走一步。
推动他们关系往前走一步的,是一只骇人的手。
一天晚上,她一不留神儿在家里摔了一跤,双脚骨折了。送到医院检查,竟查出了癌症,且是晚期。他震惊了。突然意识到,苛刻的上帝,要以倒计时的方式计算这件珍贵礼物留存在他手中的时间了。
这是她处境最为悲惨的时候——背井离乡,经济拮据,又身染重疾。她有一张躺在病床上的照片,白发斑斑,双目无神,容颜憔悴。就是在这样的时候,他爱上了她,深深地爱上了她。这位写了太多爱情传奇的作家、学者,终于有机缘幸福地将自身放进了一个真实的爱情传奇当中。
他们的婚礼是在医院举行的。新娘躺在床上,新郎坐在床沿。
婚后,他们“如一对20多岁蜜月中的爱侣”,缠绵缱绻,携手送走了一千多个美丽的晨昏。
病魔再次向她袭来,她含泪带笑地走了。
他被孤单地撇在人世间。在那些泣血的午夜,他拿起笔,真实地记录下了丧妻后的大悲大恸。
那是一本写给她看的书,也是一本写给他自己看的书。那本书,被台湾一位灵慧的译者译成了中文,书名就叫《卿卿如晤》。
他说,她离去的事实,像天空一样笼罩一切。他是那样绝望。他不敢去他们常去的啤酒屋小坐,也不敢去他们常去的小树林散步,但他又强迫自己非去不可。他失了魂魄,稍一凝神,就是她唤他的声音,如母亲唤她的婴孩……他用自己爱的触须,碰触遍了他们相爱时的丝丝缕缕、点点滴滴。太多不期然的时刻,他的老泪“夺眶而出”。
他以为自己会在这无限悲痛中度过残生了。但是,没有。他如实地告诉她,也告诉世界,在那苦痛持续了10多天之后,他像一个被锯掉了腿的病人,在安上“义肢”之后,居然拄着拐杖开始学习走路了!
他为自己心理状态的好转羞愧不已,“觉得有义务要尽量珍惜、酝酿、延续自己的哀伤”。但是,他又坚定地告诉她说,他不要那样的虚荣。他要带着“女儿兼母亲,学生兼老师,臣民兼君王”的爱妻的那颗心,遵循生活的秩序,从容地活下去。他几乎是哀嚎着告诉世人:“一切事物的真相都具有偶像破坏的特质。”——真相,惨苦的真相,不由分说地撕碎了我们煞费苦心的美丽构想,把我们不愿接受的一个丑陋结局当做礼物,猝不及防地塞进我们怀里。我们甩不掉它。我们所能做的,就是隐忍地揣了它,凭靠那被我们诅咒了一万遍的“义肢”,步步见血地赶路。
感谢他——伟大的C.S.路易斯!他为人间书写了一段最洁净无瑕的爱情;在他远远未曾爱够的乔伊走后,他用多情的笔勾勒出她“小轩窗,正梳妆”的美丽影像;更可贵的是,他勇敢地剖开自己的心,告诉乔伊,也告诉世人,他无意扮演“超级情人、悲剧英雄”的角色,他是普通的“亲人亡故的芸芸众生中的一个”,生活之水不会因岸柳的枯黄而停止流淌,日子照样还得过下去。就算是“取次花丛懒回顾”,也要硬着头皮朝前走。
所以,他在书的结尾处引用她的临终遗言,意味深长地说:“我已经与神和好。”
——每个人,不都是被生活“截肢”的独脚汉吗?“缺失感”噬啮着我们无辜的心。洗澡的时候、穿衣的时候、坐下的时候、起来的时候,甚至躺在床上的时候,对永别了的亲爱的肢体的“怀念”悄然劫掠了我们,心中的苦味决堤般涌来,让我们痛不欲生。但是,蜿蜒的路,却赶来喝令我们悲苦无告的脚,逼我们将“行走”视为必做的人生功课。——这时候,如果我们愚鲁地选择“与神为敌”,就连那走远的人,都会在冥界为我们哀哭,不是吗?
从爱之甘,到爱之憾,C.S.路易斯把他品到的爱的真滋味和盘托到我们面前。擎着这一册薄薄的《卿卿如晤》,如果我的手没有感到一种重压,我就没有资格入住C.S.路易斯苦心搭建的灵魂圣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