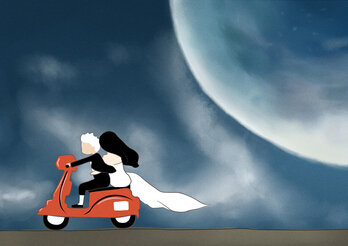
我有一个死党,他的名字叫简扬,是个男生。但是2006年4月25日的下午,这个男生因为“有要事”不能去上那节政经课,于是跪求外系的我去帮他替课。
我来到他们班的教室,坐在一个女生身边。这个女生穿一身宽大的运动服,梳着呆板的波波头,埋头睡觉,老师点名的时候,她就抬起一只手,晃晃脑袋,说明她来了,然后继续把头埋进胳膊里酣睡。她的名字很好听,叫江淑媛,偏偏人却长得又高又壮。
当然,此刻的我也好看不到哪里去,我穿着简扬那件黑夹克,戴着他的鸭舌帽,答到的时候声音比预演的还要粗犷。
放学的时候,江淑媛最后一个走。她刚走到门口,便被我抓住了胳膊。也许因为她孤独的身影让我爱心泛滥,我决定跟她交个朋友,可她竟然用力挣开我,厉声道:“你干什么!”
真是没救了,连声音也这么难听。我笑着扯下帽子:“别怕!我是女生!”
几乎同时,她转过头,也扯下头上的假发,眼神悲壮地看着我,用一种豁出去的语气说:“可是,我是男生!”
替课小组二人行
这个“江淑媛替身”,本名叫做许绍聪。后来,因为屡次替课,我和他之间达成了一个协议。他帮简扬答到,我帮江淑媛答到,这样一来,我们都不用戴假发和鸭舌帽了。
教授点名要简扬回答问题,我捅捅许绍聪:“该你上场啦!”
他回头看看我,突然径直走出了教室。教授生气地问:“刚刚那个是不是简扬?”
晚上,我气势汹汹地踢开许绍聪的宿舍门,揪着他的衣领:“你这个混蛋,你这个骗子!”
许绍聪靠在墙上,冷冷地看着我,吐出一句:“我凭什么要帮情敌的忙?”
事情复杂了。看来,我有必要去认识一下江淑媛了。
那天下午特别燥热,我皱着眉头等在车站,远远地,看到简扬拉着一个女生从长途车上下来,简扬看到我,有点儿心虚地说:“你怎么来啦?”
“你的‘要事’就是带着MM去旅游?”说完我掉头就走,走前我不忘喊一声:“江淑媛!”女生果然答应,好,确认完毕。
那天晚上,我摔烂了小酒馆的啤酒杯,大声喊着“凭什么”的时候,许绍聪来到我的面前。“凭我们喜欢他们。”他替我接续着那句话,我慢慢地看着他,“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简扬?”
“你这种女生,没勇气明说,只会暗恋,我见多啦!”
“你见多了?你见多了你还没搞定江淑媛?笑话!”
两个失意的人几乎吵了起来,最后还是许绍聪做了暂停的手势,“订个协议好不好,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把他们分开。”
许久,我点头。
如果鸭脖子有毒
简扬提着一袋鸭脖子来跟我道歉,他说:“对不起,我骗了你,但是当时我和淑媛的关系还没有确定下来,不好直说。”我挑了最粗壮的一根鸭脖子,盘腿坐在床上啃得眼皮也不抬一下:“那你们现在是生米煮成熟饭了?”
简扬嘿嘿笑着,一脸幸福的表情。我吸着鼻子悄悄埋头抹眼泪,忽然想起了许绍聪,他是不是也在悲伤地忍住眼泪呢?
我提着剩下的鸭脖子去找许绍聪,他叹着气问我:“今晚他们约会,我们做什么呢?”
最后,我们决定使出撒手锏:装病。
我跑回宿舍,擦了一脸惨白的粉底,有气无力地给简扬打电话:“你的鸭脖子,好像有毒啊,我肚子好疼,你快来救命啊!”简扬说好好好,等送江淑媛回家我就来。可一直等到日落西山,他也没有出现。我脸上的粉底都花了。
最后倒是许绍聪打来了电话。他说,我们的计划失败了,我说我病了,可江淑媛根本没来看我,估计简扬一定也没来看你吧,我握着电话的手几乎抬不起来:“许绍聪,你过来吧,我的肚子……真的……好痛。”
我蜷缩在床上,眼泪大滴大滴地砸下来,我听见许绍聪奔跑的脚步声,他说:“别怕,我马上就到了!”
只是一个小小的阑尾炎手术,我却依然感到难耐的疼痛,那不是身体的痛,而是心底的痛。
暗恋真不是人干的活儿,还没表白,就已失去。
醒来时,许绍聪靠在病床边打瞌睡,头一点一点地沉下去,像啄米的母鸡,我的动静惊醒了他,他揉揉眼睛,把我的手塞进被子:“你的手真凉,很冷吗?”
“那你呢?会不会觉得冷?”我看着他,我们的手有着同样低的温度,我们的心也都一样凉。
真心相爱的人是拆不散的
半个月后,我出院了。
我和许绍聪同时萌发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热爱,每天跟着简扬和江淑媛一起去上课。我们坐在他们两个的中间,生生地把他俩弄得天人永隔。
我帮简扬抄笔记抄得昏昏欲睡,简扬拍着我的肩膀说:“辛苦啦!放学请你吃饭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