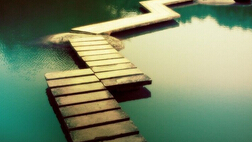
我这辈子特佩服那种活得有目的性,有方向感,冲劲十足的人。他们明确地知道自己喜欢什么,坚持什么,身上背了一条不撞南墙不死心的犟筋。就算撞了南墙,撞得头破血流也要上;撞得粉身碎骨,再拼起来打了绷带还会上。
我不行,耳根子软,心里不笃定,听人劝,吃饱饭,没事干洗洗睡了,也不长吁短叹,没心没肺的小呼噜还能打得热火朝天。
举个例子,17岁那年买羽绒服,我看上了一身火红红的长款鸭鸭,我娘偏说龟壳绿的那款更符合我的独特气质。好吧,那阵子我还是个愣头青,八字缺火也缺心眼,我跟我娘说,龟壳绿也行,就是那个绿帽子我不待见。我娘说,你看帽子是可拆卸的呀,买了吧,你一个大小伙子,穿一身红色在街上晃悠,跟一个大炮仗似的多瘆人!
好吧,那就买吧,反正我一向是个不能坚持主见的人。后来,我发现这款鸭鸭羽绒服居然是双面穿的,于是我就把我讨厌的那一面穿在里面。此后多年,鲜有人察觉,我常常在大雪纷扬的冬天,头顶一款绿帽子的内胆。
这事上,我发现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明枪明炮对着干的人,就算喜欢的路不能走,喜欢的物不到手,我也能偷偷摸摸地向我心仪的生存方式,表达某种崇高而隐晦的敬意。
到了高中文理分科时,我跟我妈的意见又出现了分歧。我妈是会计出身,后来做了人民法官,按说应该是珍爱生活,热爱文艺的女青年。可是我妈说,学文科太空泛,还是学理吧,将来搞技术,有一技之长傍身,走到哪里都能活下去。
我象征性地表达了一下自己的想法,我说,娘啊,可是我对学文是真爱啊,以后要是能做法官……
我娘立马展现出一位民事审判庭优秀调解员的基本功,笑盈盈地对我说,儿子,你宅心仁厚,公检法这种麻木不仁的地方,根本配不上你!
于是,我也笑盈盈地背上了新书包坐在理科班的大课堂里。
虽然我没去撞文科的南墙,但是也不妨碍我偷偷摸摸地跟我的学文真爱在南墙下幽会。
那阵子,我们在理科班,一样吟诗作对,一样学Bambooseven喝啤酒、白酒、葡萄酒,一样成立诗社和文学社,一样搞辩论赛和演讲比赛。不务正业的日子过得飞快,我于是顺利长成一名科大的自动化专业的新生蛋子。
大学也一样,我想泡图书馆,偏偏加入了学生会;我想搞乐队,偏偏进了篮球队。通常的情况是,我搞完联欢会,就去图书馆借本书看看;比赛赢了球,就跑上舞台唱首歌。
到了大四,又要面临择业和考研。
我娘说,你上班吧,家里条件不好。我在电话里说:“好的。”放下电话就给自己报了一个辅导班——还是法律硕士的考研辅导班。
由于这辈子头回瞒着家里干这样的大手笔,每天鸡贼地勤奋得不行。那时候,班上到处青春靓丽、求知若渴的女同学,一个假期的辅导班上下来,我愣是一个姑娘的名字都没问来。
统考过后,我问我娘,要是我能上研究生怎么办?
我娘说,没事,真是能上,把咱家里房子卖了把你供出来。
我因为大学成绩还说得过去,比较顺利地在一家研究院找到了工作。等到出了成绩,不等我娘卖房子,我就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把录取通知书自行了断了。这辈子,坚持自己喜欢做的事情,最坚决、最接近的一次,就这么静悄悄地溜走了。
于是我就进了这家研究院,根红苗正的工科男,从此一门心思地搞技术——当然,这是不可能的。我在检验检测、鉴定评审的同时,开始慢慢地写随笔和小说,甚至后来在读研深造的那几年也一直没有放弃。两手都在抓,两手都不软,如果写出一篇技术论文,就马上奖励自己写一篇小说;如果随笔发表了,就想着能不能申请一个技术专利。
米兰·昆德拉在小说里写:“生活在别处。”仿佛天堂永远是住在我们隔壁的某个地方,伸开双臂,无法碰触,踮起脚尖,遥不可及,一个庸俗的肉体茫然无措又事B兮兮。而我又是那种天生软柿子的人,一辈子不想坚定不移地朝着自己喜欢的方向冲,不想犟筋,不想撞南墙,不想热泪盈眶。
我只能说,我喜欢偷偷摸摸地向我喜欢的生存方式表达敬意,苟且偷生,好死不如赖活着地爱着,羞怯着,骚扰着,在不能中不舍,在不舍中不执。后来我知道,没学文也挺好,一样阳光普照,后来我知道,没读研也挺好,一样带雨春潮。到最后,我发现我居然成了学生会里最会写小说的,写小说里最会打篮球的,打篮球里最会唱卡拉OK的那个人的时候,这个世界奇妙了。
有些幸福和认同注定不是拼来的。天堂在左,肉身在右,与其四顾无望地茫然追逐,不如凿壁偷光,让自己活得柔软而敞亮。